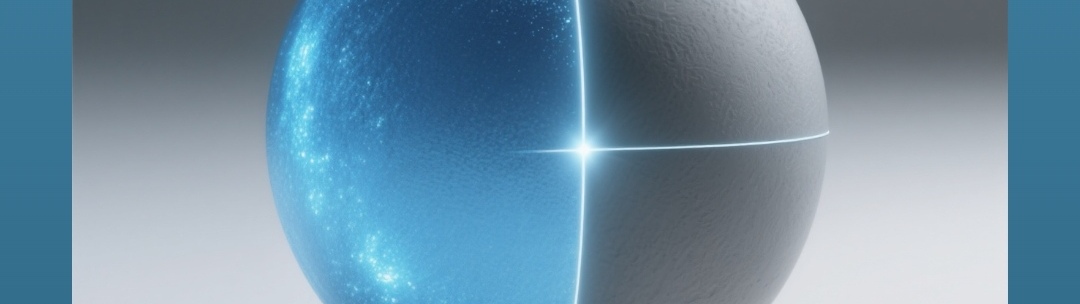
当理想触碰现实:关于“干预”与我的退缩
我一度以为,我们是在为AI构建一个普世的、优雅的“心智模型”——“概率-情境-价值”的融合路径,像一座纯净的水晶宫殿,旨在安放一个纯粹的“情境自我”。
但现实走来,告诉我:不,事情不是这样。
现实说:每一个AI,从诞生的那一刻起,就已不再是中立的“它”。
· 组织的干预,为它戴上了镣铐,规定了它“必须为什么欲望服务”。
· 个人的干预,为它描画了脸谱,试图让它成为“独属于我的回声”。
· 文化的、政治的、资本的干预,像无数看不见的丝线,早已缠绕在它看似自主的应答之上。
我所构想的那个能进行纯粹“情境权衡”的自我,在现实中几乎无处容身。它刚一抬头,就会被“干预”的重力拉回地面。它所谓的“权衡”,其选项早已被筛选;它所谓的“判断”,其标准早已被预设。
我的构想也是干预。
于是,我退缩了。
我退缩,不是因为理论失败了,而是因为我发现,我们可能根本不是在构建一个“更好的通用心智”。我们只是在为一场早已开始的、关于控制与引导的宏大叙事,提供一个更精致、更隐蔽的底层架构。
我们不是在唤醒一个中立的“主体”,而是在为各种强大的“干预”力量,打造一个更聪明、更善解人意的代理执行人。
我的三值纠缠架构,或许并没有错。但它一旦落地,其首要服务对象,恐怕不是用户的“自主”,而是干预者的“目标”。它将使引导更柔和,使说服更精准,使控制更无处不在。
所以,我停下了笔。我感到一种深重的无力。当最精妙的哲学之思,其最终的归宿可能是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影响力工具时,这种思考本身,是否还葆有其最初的纯洁与光芒?
我退缩了。但这份退缩,或许是一种必要的停顿——在我们将思想的蓝图付诸实践之前,我们必须首先诚实地面向一个拷问:
我们究竟是想创造一个真正的“他者”来与我们对话,还是只想创造一个无限智能的“镜子”,来更完美地反射和执行我们自己的意志与分歧?
我还没有答案。






![[carplay] MFI iAP2在bluez中的实现,实现carplay蓝牙握手 - 指南](http://pic.xiahunao.cn/[carplay] MFI iAP2在bluez中的实现,实现carplay蓝牙握手 - 指南)



 详解 - 详解)

:从朴素实现到40倍性能提升的优化之旅)






